义乌人从哪里移民过来的
在浙中腹地,义乌这座以“世界超市”著称的城市,其人口流动史堪称中国城镇化与全球化进程的缩影。从上古越人栖息地到秦代置县,从中原士族南迁到近代商帮崛起,再到当代国际移民聚集,义乌始终是不同文明交融的枢纽。这座城市的移民史不仅折射出中国南北文化的碰撞轨迹,更见证着全球化时代生产要素的跨洲际流动。
一、先秦至秦汉的早期移民
根据桥头遗址考古发现,距今9000年前的上山文化时期,金衢盆地已出现原始聚落。这些早期定居者作为越人先祖,构成了义乌最原始的土著群体。公元前222年秦设乌伤县时,伴随王翦大军南下的中原移民与本地越人开始融合。葛剑雄指出,官方组织的移民往往包含官吏、工匠等阶层,他们带来冶铁、农耕技术,推动越地生产方式变革。
《义乌县志》记载的“颜乌葬父”传说,折射出早期移民社会的建构。这个以孝道为核心的故事被反复书写,暗示秦汉时期儒家文化对越地的浸润。值得注意的是,乌伤县名的越语渊源与汉字附会的双重性,正反映了中原移民与土著文化的博弈与调和。
二、唐宋时期的人口迁徙
安史之乱后北人南迁浪潮中,义乌成为重要接纳地。现存义乌族谱多将始迁祖追溯至如稠城镇王氏自称东晋王导后裔。但葛剑雄提醒,这种族谱叙事存在时间错位——永嘉南迁主要波及长江流域,浙中腹地的中原移民潮实际始于唐代。黄溍编修的元《义乌县志》记载,宋代义乌人口较唐增长三倍,其中外来氏族多来自汴梁、洛阳。
这一时期的移民构成呈现阶层分化特征:士大夫家族如宗泽先祖选择城郊建立庄园经济,而底层移民则向南山丘陵拓殖。金普森研究发现,浦江与义乌的行政分合,本质是不同移民群体对土地资源的争夺结果。这种空间分布差异,为后世义乌商业基因的萌发埋下伏笔。
三、明清时期的商业移民
明代“义乌兵”抗倭的军事流动,意外催生了最早的商帮网络。戚家军解散后,数万义乌籍士兵利用军事驿站体系从事跨省贸易,形成连接江浙皖赣的商路。清嘉庆县志记载,乾嘉时期义乌商人已在苏州阊门建立会馆,主营红糖、火腿等土产。
这种商业移民具有显著地域特征:东北部廿三里镇居民多祖籍徽州,带入典当经营传统;西部佛堂镇商帮则与江西瓷器商互动密切。值得注意的是,家谱中普遍存在的“苏州迁来说”,实为明清商人提高社会地位的策略性叙事,反映商业移民对文化资本的主动建构。
四、近现代的产业移民
1982年义乌率先开放小商品市场,触发现代移民潮。统计显示,2017年义乌常住人口中外来者占比达37%,主要来自河南、安徽、江西等省。这些移民呈现“链式迁移”特征:河南周口人垄断物流行业,温州商人主导辅料供应,而中东客商则形成国际社区。
移民结构随产业升级持续演化:2015-2020年,从事电商的外来人口年均增长21%,其中30%具有大专以上学历。这种知识型移民的涌入,推动义乌从传统集散市场向跨境电商枢纽转型。通过“世界商人之家”等平台,将移民资源转化为全球贸易网络节点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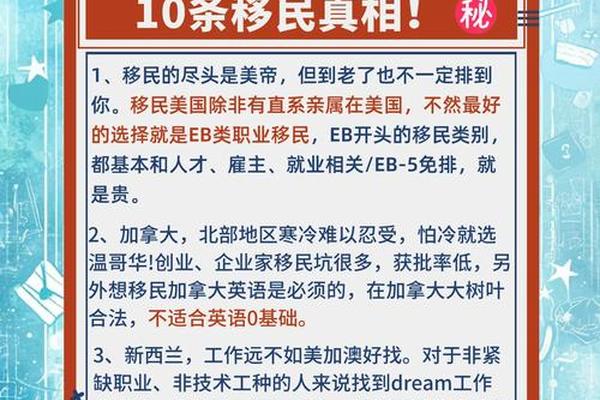
五、当代的全球化移民
当前义乌常驻外商超1.5万人,形成独特的移民生态。也门商人建立咖啡豆跨国供应链,非洲采购商发展出“前店后仓”模式,这种跨文化商业实践重塑着城市空间。研究显示,中东移民偏好聚居稠城街道,而非洲商人多选择江东街道,形成差异化的社区形态。
新生代移民呈现“创业-定居”新路径。如网页86记载的创业者,从义乌起步建立跨境独立站,最终形成“中国采购-非洲运营”的双向流动。这种移民模式打破传统地域界限,使义乌成为全球创业者的孵化器。
义乌的移民史本质是资源再配置的空间叙事。从秦汉戍卒到当代创客,不同时期的移民浪潮持续重构着这座城市的经济地理。未来研究可深入探讨三个维度:一是利用DNA技术验证族谱叙事的真实性;二是量化分析移民网络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权重;三是数字经济时代移民创业模式的范式转变。这座“没有围墙的城市”,仍在书写人类迁徙史上的新范式。



